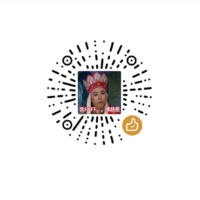这个春节,大家肯定过的很憋。不知道有几个人已经宅到要抓狂了?
但是啊,这一幕,其实32年前,上海就出现过了。而且当年很多细节,也都完全一样。

看看当时的报纸。
当时是上海出现了大规模的甲肝流行现象。起因呢,也是祸从口入。
不过那时候上海吃的只是毛蚶。其实就是一种贝类。

本来这玩意也没啥不能吃,但是忽然间从启东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毛蚶生长地,比过去从山东弄的便宜很多,于是大家就大吃特吃。
然后就杯具了。
当时的数据也很有趣:
1月18日:43例
1月19日:134例
1月22日:808例
1月23日:1447例
1月27日:5467例
1月31日 :12399例……
偏偏天气又反常,大寒的时候上海依旧是暖洋洋的,为流行病的传播添了把柴。
到2月1日,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。
当时的病人也和今天一样:
上海各家医院都有大量病人涌入。
他们大都出现了身体发热、呕吐、乏力、黄疸等症状。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了。
当时上海人住房面积狭小,有些人担心传染给家人,又怕医院没有空床位,骑着自行车,带着折叠床、被子就来了,要求立即住院。
只是还好,甲肝不会通过飞沫传播,基本不会继续交叉感染。但是,一样很多正常吃坏肚子的,着凉的也来排队。
其结果,当然也是医疗资源紧张,床位不够用了。
隔离的事情,也是一样:
当时上海各家医院所有的病床全部加起来,也只有5.5万张。而每天新增的甲肝病人,数以千记。
前面提到的寿幼森夫妇和蒋建新被查出甲肝的时候,恰恰是高峰时期。
所以,他们均被要求回家“自我隔离”,定时来医院配药、验血。
“我有老同学、老同事生过这种毛病的。我印象里,一有这种毛病就被关进医院隔离病房了。”寿幼森说。
“我被查出来以后心想:是不是我也要被关进去啦?人家讲,侬想也不要想了。”
寿幼森住在富民路上的新式里弄里。
听说夫妇俩患上了甲肝,住在楼上的父母和哥哥都有点“警惕”。
“因为阿拉卫生间是共用的。”他说。
“当时姆妈有个老保姆,也是阿拉弄堂的,言话多煞了。阿拉夫妻俩只好缩在亭子间里不出来。”
而那时候对人的警惕,防备,也完全和今天一样:
“走在马路上,人家不停地在看侬面色。假使侬面孔蜡黄,人家肯定躲得远点。”寿幼森说。
上海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,熟人见面也不握手了,更不敢互相敬烟了。
关于疫情蔓延的流言传遍大街小巷,使人惶惶不可终日。
对甲肝的恐慌心理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各地,导致其他省市排斥上海人的现象。
最玄幻的是,连吃药都一样:
其实,甲肝是一种可以自愈的疾病,治疗方法主要是卧床休息,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、维生素C,每两周查一次血。
但病人不吃药就不安心。
于是,谢丽娟“发明”了一种“大锅药”:把茵陈、甘草、大黄等中草药放在一口大锅里煮,到吃药的时候每人分上一碗。
“说实话,每人喝的这碗药里究竟有多少药的剂量,我们并不去计算它。这是一方‘安慰剂’。”谢丽娟多年后接受访谈时说。
所以嘛,昨晚有双黄连的事儿出来,我一点儿也不奇怪。
另外,圈内有人跟我,对我这儿读者对双黄连信不信有分歧,那老规矩,咱们来投个票。
注意,别投错。
我倒是要看看比例。
另外,黑格尔那句话说的真好:人类是从历史上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不会吸取教训。
日光之下,并无新事,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,基本都会再发生。
还记得我新年献词说的吗?让普通人大家苟住,保住工作是最重要的。当时估计很多人还觉得懵逼,觉得不以为然。你今天再看看,怎么说?
央妈咪啊(我这个咪故意加的),该投降了。
蒙古大夫,该投降了。
至于红会,别再问我了。我昨天文章《大家用力悠着点哦……》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?你们再怎么说,人家就是聋子不怕响雷打,死猪不怕开水烫。今天不就继续秀下限给你看嘛。
而且啊,我看他马上就要出来哭夭,说什么人手不足,经费不足,请求扩大编制,增加经费,来继续诈……不对,继续“服务”咯。
(PS:芥末圈的人注意,今天下午其实还发了个文,但是被404了,那个文章我扔置顶的旧文合集里。可以自提。以后副是一个合集包,其他的在那边。)
更多交流,请关注芥末圈(孤苑白首二十年已经完本,共221章正文+9外篇,近50万字;试读请点击《孤苑白首二十年(1)》;副教主倒灶系列已经更新至101章,试读请点击《【黑木崖系列】副教主倒灶(22)》)